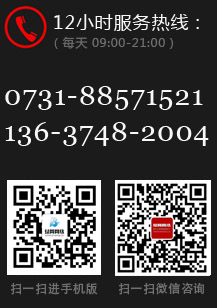今日圣誕,預示著2018年即將過去。讀書君的朋友圈里紛紛曬出了自己的“2018年總結”。這一年,是否也有什么人和事給你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呢?可以在后臺留言告訴我們哦。
每年一到這時候,看城市火樹銀花,到處都是濃濃的圣誕氣息,腦中關于圣誕的記憶就會自動點亮。某個恍惚的瞬間,你是否會想一想,曾陪你一起過圣誕的那些人,還在你身邊嗎?他們現在都怎么樣了?
下面的三篇文章,來自青年作家鄭執、詞人林夕和美國作家卡波特。和我們一樣,他們的記憶中有美好,也有遺憾。但無論如何,過去的時光永不復現,我們只能跌跌撞撞,收藏那些美好如握緊手中的硬幣,跨入2019年的門檻。
北方沒有圣誕節
文| 鄭執
五年前的圣誕節,我在香港吃了一頓免費的圣誕晚餐,拜朋友亨利所賜。我們原本不熟,后來卻因為在同屆畢業生里成為最后兩個找工作困難戶而結緣。工作沒著落的半年里,我們整天為錢犯愁。 亨利雞賊,每次逛商場時都去豪車店或珠寶店里逛,問東問西裝大款,店員就會留下電話資料,逢年過節邀請客戶參加免費沙龍或party,總能接到電話,還可帶人同行,那年圣誕帶的是我。當晚我們喝了不少免費香檳,喝多了湊錢打車回到亨利家又餓了,煮了包速凍餃子配劣質紅酒。亨利跟我都是北方人,餃子吃不膩。亨利說,自己小時候從來不過洋節,印象中不管什么節日都得吃餃子,他理解的過節,就是有人陪你吃餃子。 那不久后,我找到一份勉強糊口的工作,一年后的圣誕節,公司聚餐,香港人過圣誕的氛圍濃,我像個外人,不好舔臉放開吃,回家又煮了袋速凍餃子。從那以后,每年圣誕節我都吃餃子。日子過得不好,聯絡越來越少,亨利具體哪年離開的香港我都不知道。 有人給亨利算命,說他最適合呆在四面環水的國度,后來亨利去了菲律賓。有一次,收到他醉酒發的微信:“我猜你應該在北方。”那時我剛剛搬到北京。但是他自己再也沒回到北方。三個月以前,他騎摩托車出了車禍,人生最后一張照片定格在朋友圈。又快到圣誕節了,一個我從來不過的洋節。距家兩公里外的商場巨幕里每晚都有麋鹿拉著圣誕老人狂奔,而我就在北方,盼一場雪的愿望被霧霾驅散,不敢出門,外賣叫來一包速凍餃子備好。過節必須吃餃子,不管什么節都好。曾有朋友問過我,過節為什么不能想點開心事?我無言以對。團聚本來就是一種形式,用來緬懷再也無法歸來的人的形式。 今年圣誕,我猜亨利應該也在北方。而我會在家煮餃子,毫無懸念。
原發“ONE·一個”,作者授權轉載
那年圣誕,我像一個壞人
文| 林夕
盤點歷年圣誕除夕新年如何度過,沒什么意思;因為有意思的事情,不一定就那么巧合,在節日里發生。但節日也像金錢一樣,摯交以至伴侶之間,重點不是金錢,但錢字卻往往是一面你最不想看到的照妖鏡,或是照見人性善良面目的湖水。再不重視節日,節日卻總定時向你做出民情報告。
有年人在內地,過幾天就是圣誕,再過幾天又有工作,就索性留在那里更省事。同行的人都有家累,有義務要回港交人,為與他們沒有什么瓜葛的主耶穌慶生。我堅持一動不如一靜,一個人留在那里,花了許多唇舌才說服他們,準我留下來吧。
我留下來,當地一個朋友非常熱情,一定要陪我過圣誕,但是要先去參加朋友的聚會,然后可以早退,回來與我吃飯。我又花費了好多唇舌,表示沒關系,我不愿意讓對方一腳踏兩條船。對我來說,身在曹營與人周旋,心卻牽系著另一個地方、什么時候趕赴另一場約會,是自找煩惱。可是,明顯對方很習慣而且頗享受趕場子的樂趣,所以比我更堅持。于是只好等,我不怕等待,如果能說得準一個時間,哪怕再長,也還有大把事情可做。偏偏像這等情況,大家也只能大約在幾點,大約是最令人忐忑的,雖然那個人不是誰,又因為那個不是誰,所以更不值得。
我打開隨身帶來的一本小說,看得津津有味,然后,心里萌生了一個歹念:千萬,千萬別那么早回來,我正樂在其中,別腰斬我的樂趣,等一下實在難以分神,從小說一下子跳回現實。不久,肚子有點餓,于是我就隨便點了酒店一碗牛肉面吃。剛吃著,那人剛好趕上,見我在吃面,更一臉內疚,看得我也內疚起來。那人說,圣誕該吃圣誕餐噢,我說,酒店菜單里的確有這套餐,不過我更愛吃牛肉面,圣誕快樂,不是應該快快樂樂地愛吃什么就吃什么嗎?那人堅持要再點一個標準的圣誕餐,但是他又已經在別處吃撐了。
這二人圣誕集會的結果是,那人看著我勉強把圣誕餐吃掉,為了不辜負他的盛情,我得很用力地吃給他看,表情非常生動。正當我有點擔心,吃完之后,我的小說還如何能繼續,誰知,那人卻已無聲無息地在電視聲浪中睡著了。他醒來之后,也實在太疲乏了,沒聊到幾句,就互祝一聲,打道回府。我有點慚愧地偷偷松了一口氣,沒想到,這慚愧之心,卻在那人走后,影響到我連小說也看不下去,因為我自覺好像在嫌棄人家真心的熱情,我從來沒有這么像一個壞人。
如果不是為過節而過節,我們大可悠閑地吃頓飯,談談天,最終,熱情卻成為彼此的牽累,何必。從那以后,稍微有點勉強的聚會,安排有點需要費心思的所謂節目,我都一概放棄,節日讓我學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選自《任我行》,林夕著
圣誕節憶舊(節選)
文| [美] 杜魯門·卡波特譯| 潘帕
想象一下十一月底的一個早晨。二十多年前冬天來臨的一個早晨。設想邊遠小鎮上一座四散延伸的老房子里的廚房。黑色的大火爐是這個廚房的一大標志,但廚房里還有張大圓桌,壁爐前放著兩把搖椅。今天壁爐發出季節到來的呼叫。
一個白頭發剪得很短的婦人站在廚房的窗前。網球鞋,夏天穿的印花布裙外罩一件不成形的灰毛衣。她個頭很小,精神飽滿,像只矮腳母雞;但由于小時候的一場病,她的肩膀有點佝僂,怪可憐的。她的臉很獨特——和林肯的臉不無相像,一樣因風吹日曬而略顯粗糙,但很精致,骨肉停勻;眼睛像雪利酒一樣的色澤,怯生生的。“哦,老天,”她大聲說,呵出來的氣煙霧般彌漫在窗玻璃上,“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氣。”
她對誰說話呢?我。那時我七歲,她六十多了。我們是表親,很遠的表親。從我記事起,我們倆就住在一起。房子里住著別的人,就是一些親戚。他們有權對我們發號施令,還常常把我們弄哭,但大體上我們倆不太在意他們。我們是彼此最要好的朋友。她叫我“巴迪”,為了紀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。那個巴迪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死了,當時她還是個孩子呢。她現在也還是個孩子。
“我沒起床就知道,”她從窗邊轉過來,眼中閃動著興奮,意味深長。“教堂的鈴聲又冷冽又清楚。鳥兒也不唱了,它們都飛到暖和的地方去了。肯定是的。哎,巴迪,別吃餅干了,去推我們的小推車。幫我把帽子找出來。我們要烤三十個水果蛋糕呢。”
一直都是這樣:十一月一個早晨到來,我的朋友仿佛代表官方,宣布這年圣誕季的到來。對節日的想象使她精神振奮,心中的火焰因為圣誕季來了而燃燒:“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氣!去推我們的小推車。幫我把帽子找出來。”
……
圣誕節前一天的下午,我們搜刮出一分錢,去肉店買送給奎尼的禮物,老傳統:一塊尚有余肉可咬的牛骨頭。用彩紙包起來,高高地掛在圣誕樹頂上那顆銀星邊。奎尼知道它在那兒,饞得坐在樹下呆望著,到該睡了都不肯走。其實我和她一樣興奮。我踢掉被子,玩轉枕頭,像在大熱天似的。不知哪里一只公雞叫了:假情報,太陽還在地球那一頭呢。
“巴迪,你醒著嗎?”我的朋友在她的房間里叫喚我,就在我隔壁。一會兒,她手握一只蠟燭坐在我的床邊了。“哎,我根本睡不著覺,”她說,“我的心像兔子一樣亂跳。巴迪,你說羅斯福夫人會在晚餐時端上我們的水果蛋糕嗎?”我們倆在床上擠成一團,她在我的手心里寫“我愛你”。“你的手比以前大了。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長大。你長大了以后,我們還能繼續當朋友嗎?”我說我們永遠是朋友。“但是我覺得很難過,巴迪。我多希望能給你輛自行車。我差點賣掉爸爸給我的那塊浮雕寶石。巴迪——”她遲疑了一下,似乎有點難為情,“我又給你做了只風箏。”
我也承認我也給她做了風箏,于是我們大笑起來。蠟燭燒得太短了,手沒法握住,漸漸地熄滅了。只有星光閃爍,星星在窗上打圈,仿佛在唱圣誕頌歌,很慢很慢地天亮了,靜下來了。我們大概都迷迷糊糊睡了,但晨曦像冷水潑到身上一樣把我們叫醒了。我們起床,睜大眼睛,四處游蕩等家里別的人醒來。我的朋友故意失手讓水壺掉到地上;我在緊閉的門前大跳踢踏舞。房子里的人一個個都出來了,臉上的表情像是要把我們倆都宰了;但他們不能,因為是圣誕節嘛。首先是豐盛的早餐:你所能想到的都有——從煎餅到炸花鼠,從玉米片條到蜂蜜。人人都吃得心滿意足,除了我和我的朋友。說實話,我們實在是等不及想去看我們的禮物了,幾乎一口飯都沒吃。
唉,我很失望。誰能不失望呢?幾雙襪子,主日學校的襯衫,幾塊手帕,別人穿不下了給我的毛衣,一份針對兒童的宗教雜志一年的訂閱,叫小牧羊人。真叫我生氣,真的。
我的朋友的收獲比我好。一包薩摩蜜橘,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禮物了。她最引以為傲的是一條白羊毛圍巾,她已婚的妹妹織的。但她說她最喜歡我給她做的風箏。確實滿漂亮的,雖然沒有她給我做的那只好看。她給我做的風箏是藍色的,點綴著金色和綠色的星星,那些星星用來表彰表現良好的孩子,上面還寫著我的名字“巴迪”。
“巴迪,起風了。”
起風了,我們不做別的,就是跑到房子后那片草地上,奎尼一溜煙跑去埋肉骨頭(一年之后,奎尼自己也要被埋到這里來了)。我們在齊腰的長勢很好的草中穿梭,放飛風箏,手心感到它們的拉扯,仿佛它們是天上的魚,悠游在風中。太陽曬得我們暖洋洋的,心滿意足,躺在草叢中,剝橘子吃,看著風箏在天上搖曳。一瞬間,我忘記了襪子和別人穿過給我的毛衣。我高興得好像我們中了咖啡取名大賽的五千塊獎金。
“天啊,我多傻啊!”我的朋友大叫起來,像個忘記烤箱里在烤餅干的主婦一樣,突然警覺起來。“你知道我常常怎么想嗎?”她的語氣好像發現什么,朝著遠處微笑,沒看我。“我一直以為,一個人要生病,臨終了才會看見上帝。我以前想,上帝來了,就像是看著浸禮會教堂的窗玻璃一樣:陽光照耀下,五彩繽紛,光彩奪目得你忘記會天黑。很舒服的感覺:設想那光亮帶走恐懼。但現在我覺得那壓根兒不會發生。我覺得上帝早已顯靈,不是到了人要死了才那樣。就是那樣”——她的手在空中劃了個圈,把云朵,風箏,草地,還有在刨土埋骨頭的奎尼都劃進去——“就是那樣,我們平時看到的一切,上帝都顯靈其中。對我來說,我今天看到這一切,可以滿足地離開這個世界了。”
這是我們一起過的最后一個圣誕節。
生活把我們分開了。那些無所不知的人認為我該去上軍校。這樣,我進了一個接一個軍號作響的監獄,無情的起床號響個不停的夏令營。我也有了新家。但那不算數。我的朋友在哪里,哪里才是我的家,而我再也沒回去過。
她還是待在那里,在廚房里度過時光。孑然一身,有奎尼做伴。不久就只剩她自己一個人。(“親愛的巴迪,”她潦草的字跡寫道,“昨天,吉姆梅西的馬踢傷了奎尼,傷得很重。謝天謝地,她沒有太痛苦。我把她包在一張條紋床單里,用推車推到辛普森家的草地上;在那里,她可以和那些肉骨頭在一起……”)。
接下去那些年的十一月,她還是做水果蛋糕,就她一個人。沒有以前做的那么多了,但也不少:不用說,她總是把“最好的那個”寄給我。
同樣,每封信里她都放一枚一毛錢硬幣,用衛生紙包得好好的:“去看電影,回頭寫信告訴我故事情節。”但漸漸地,她在信中把我和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死去的那個巴迪混淆起來;每個月不僅僅是十三號那天,她在床上起不來了:在十一月的某個早晨,一個樹枝光禿禿,鳥兒不再鳴叫的早晨,她再也無法起床,大聲宣布:“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氣!”
這事發生時,我就知道了。通知我的信只是證實了我的感覺。某種隱秘的情緒使我早早感知到了;同時,我生命中無法被取代的一部分被切斷了,就像斷線那頭的風箏一樣。所以,那年十二月的那個早晨,走過校園時,我一直看著天空,眼睛不斷搜尋著,仿佛期待看到心像兩只斷線的風箏一樣,向天堂飛去。
選自《圣誕節憶舊》,譯林出版社出版